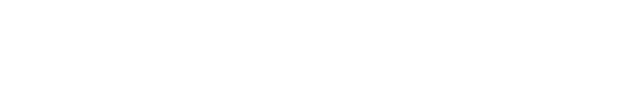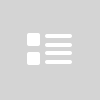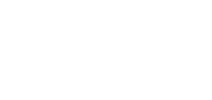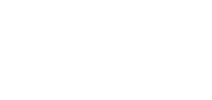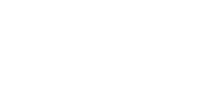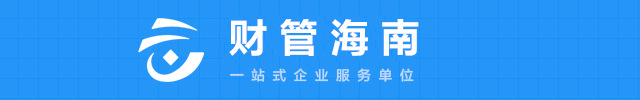
“经济人”假设的演变与发展
发布时间:2025-05-23
“经济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虽然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各种批评,但其基本核心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经济人”假设的演变与发展
近代才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性。孔子指出,人们有追求财富、逃避贫穷的心理倾向:“财富和财富是人们想要的”,“贫穷和廉价是人们的邪恶”。荀况详细讨论了人性,并提出了一些关于人性的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性的:“凡性,天也,不能学,不能做。(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姚、舜、杰、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性是邪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呢……;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性“见利不可就,见害不可避。它的商人通贾,双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利在前也。渔民入海,海深万人,彼逆流,乘危百里,夜不出,利于水。故利之处在于,虽然千山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由此可见,《管子》已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然而,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简单明了,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的概念不能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早期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想法:每个人自由的自由活动自然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其效果远远大于非自我利益的活动。他指出:在蜜蜂社会中,如果(被认为)不良和奢侈,那么社会就会繁荣;如果(被认为)道德和简单,那么社会就会忽视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成为社会动物的原因不是友谊,不是善良,不是同情,不是假装的善良,而是他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是使他适合这个最大、世俗、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部严格的经济学作品。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最初将“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起点•斯密。在《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研究》中,他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帮助。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别人的恩惠。如果他能刺激他们的自我利益,使他们受益,并告诉他们,为他工作对他们自己更有利,他就更容易实现他们的目标。不管是谁,如果要和别人做生意,他首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请给我你想要的,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计划。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而是说唤起他们的利己心。我们不说我们需要什么,而是对他们有好处。但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违背常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不同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我们还必须假设“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在斯密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假设,隐含在对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个行动都不是出于任何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可以从利益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在斯密,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也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人们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他们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利益。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不考虑社会利益,而是考虑自己的利益。然而,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可避免地引导他将资源应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目的。因此,埃奇沃思将人的行为被自身利益驱使为“经济学第一原理”。